午夜醒来,我梦到了故乡。
故乡还是记忆中的故乡,依然是“暧暧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……”安静的模样,让人沉醉。
我透过家里狭小的窗户,看着眼前这个城市。远处高楼林立、灯火通明,让人恍如置身于一个庞大而虚幻的梦境。夜色中,无数明窗格子如蜂巢,而我就是那忙忙碌碌的蜂,日复一日,在陌生的巢房之间奔波。
我从哪里来、要到哪里去,成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。故乡早已成了梦中的故乡,那里没有我的半分田,亲人已经离我而去。偶尔回去一趟,有人会以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姿态问我。而城市也只是我的暂居地,自从年轻时背井离乡到外地求生,我就一直辗转于各个城市间。我在城市间游荡,只是为了生存。
年过半百,我活成了无乡之人。
想想,现在的我有多么想回到故乡,以前就有多么想逃离故乡。我的故乡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大山里,每天看到的除了山还是山,曾经年少的我没事就喜欢坐在山峁上看山,想象着大山外面的世界。
离开老家时我只有十几岁,我到镇上读中学。背着铺盖卷走的时候,母亲站在院门口的枣树下,手搭凉棚送我,微风送来母亲的话:“不要想家,到了镇上要好好读书!”我明白母亲的意思,我是山沟沟里农民的儿子,读书是我逃离大山唯一的出路。不要母亲嘱咐,我早已经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所以第一次离开父母,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,我没有伤感,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。我终于要逃离大山。现在回头,我想到了院门口的枣树,想到了送我的母亲,丝丝伤感和暖意夹杂着扑面而来。
后来我辗转到省城读书,胡同里的风灌进我租住的小屋,常常冷得我夜不能寐。我缩在异乡的冷寂里,想起家乡那缕缕的炊烟。
炊烟是我对故乡最强烈的记忆。清晨,家家户户的烟囱中升起袅袅炊烟,小山村苏醒了,忙碌开始了。然而近些年来,我每次返乡回故里,愕然发现那熟悉的气息不知何时已经陌生。我像一棵被移植过的树,根须已经被剥离,尽管重新栽回故土,可似乎失去了当初的血脉相连。
毕业后,我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在各个城市间漂泊。渐渐地明白,所谓故乡,留不住我的肉身,为了生活我不得不背井离乡;而城市又无法融入我的灵魂,故乡的炊烟时不时闯进我的梦里。没有了归属感,灵魂和肉身就一直在流浪。我如同许多人一样,不再是从此岸出发到彼岸的人,而是背负着“半故乡”在赶路的人。
也许归属感这枚印记,既非被某一处土地永久刻下,也不由一纸户籍来决定。它在异乡的一缕熟悉的气味里苏醒,在迁徙轨迹上的每一处短暂停留。我们这些如蒲公英飘荡的异乡人,在故土与城市中一次次回望与融合,用身体丈量两者的距离。
有人说:成长就是逃离故乡,又想回到故乡。逃离是因为诗与远方,是为生活努力,是拼命扎根。
故乡是一种想念,想念远方没有的温暖,没有热乎的饭菜,没有人情可靠,没有牵挂牵绊。
我们离不开远方,也离不开故乡。一方代表生活,一方代表怀念。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孩子,就成了不伦不类的“半故乡”之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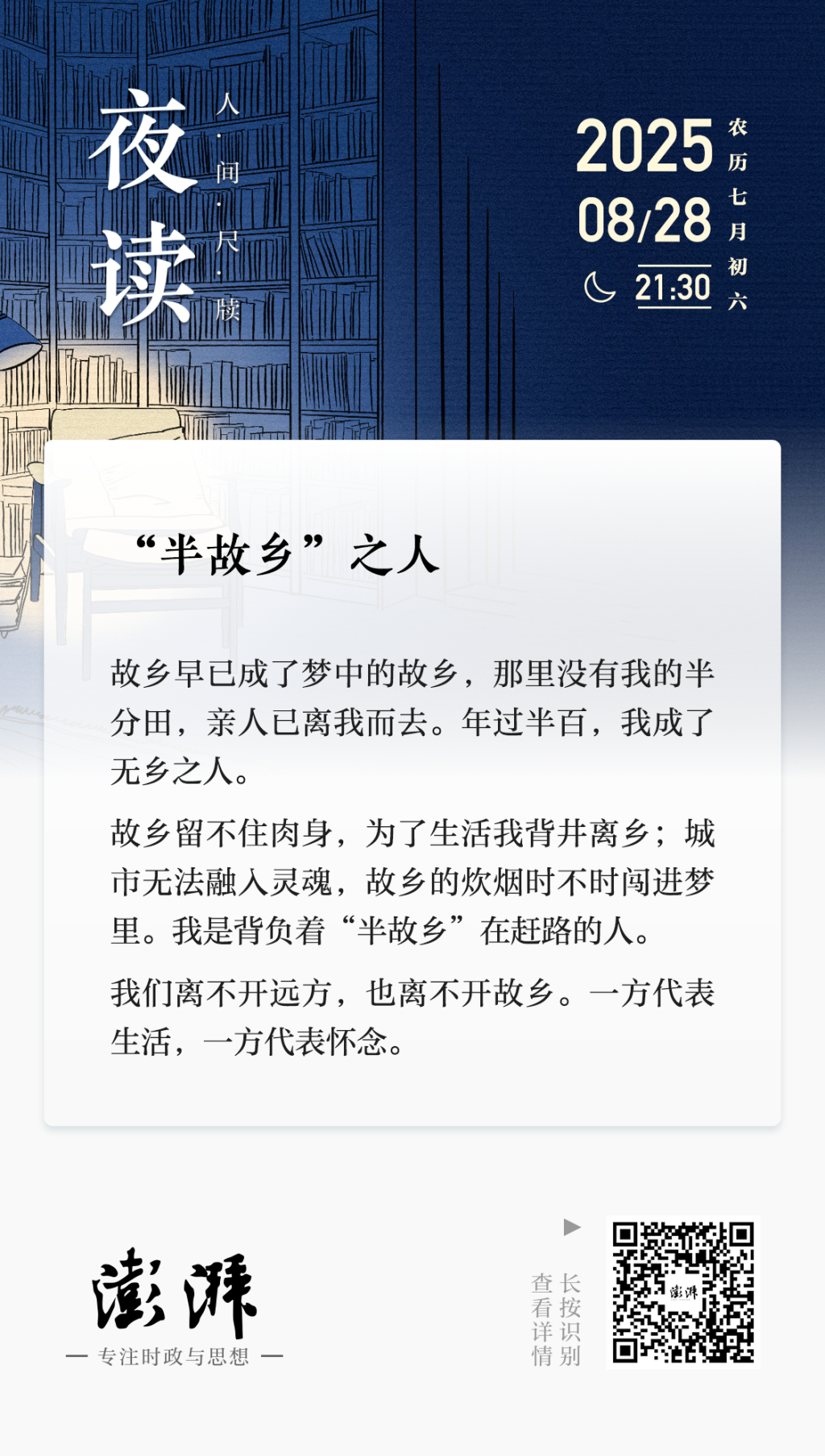
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夜读丨“半故乡”之人》








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15
京ICP备2025104030号-15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