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编者按】
五十年春风化雨,中欧从相识到相知,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。“志合者,不以山海为远”,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,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,更是两大力量、两大市场、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、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。
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,澎湃新闻推出《再遇见——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》,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,通过他们的亲历、记忆与洞见,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、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。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,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。
这一次,我们对话的人物是:中国社会科学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。

“使命感是我们这代人所特有的一种动力,总会有一种‘应当去做’的驱动力。这种动力,加上兴趣,加上求知的欲望和求知的方法,就会有一种‘恨不能为之’的感觉。”2021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弘在自己出版的《在“茶”与“咖啡”之间》的《余言》一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。
“如果陈乐民先生(编者注: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,是中国首倡‘欧洲学’的学者)现在还在世,他问我‘你的欧洲学怎么样了?’我会告诉他,欧洲学已经初见规模。”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,周弘带着很自豪的语气告诉记者。
从1979年进入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开始学术生涯,到1986年调入欧洲研究所开始欧洲研究,周弘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跟欧洲打交道。“我是学西方现代哲学的,然后转到学习西方现代思想史,这些都和当代欧洲密切相关,从哲学所调到欧洲所,对我来说是专业更加对口。”
除了学者的身份,周弘还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委员。“在人大的工作,更多是在学习,同时,我们也接待过一些来自欧洲国家的议会代表团,反过来加深了我们对欧洲问题的理解。”
“大家对中欧关系都是充满期待的,”周弘表示,“数千年来,不管山川大漠的阻隔,还是战争和政治的破坏,中国和欧洲都在不遗余力地接触对方,我对中欧关系向前、向好发展是没有异议的。”
中欧“要尽可能多地恢复交流渠道”
澎湃新闻:您从事欧洲研究也有将近40年时间,也见证了中欧从建交初期到双边关系提升为“全面战略合作伙伴”,再到2019年欧盟提出中欧关系“合作、竞争、制度性对手”“三重定义”的各个关键节点。您如何看待中欧关系50年来的这种变化?其中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?
周弘:我们现在讲的中欧关系50年,实际上是中国和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50年。中欧之间交往的历史是远远超过50年的,有上千年的历史。
自从1975年中欧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,双方关系处于上升期,直到2003年,中欧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在这一时期,中国与欧盟之间是实现了相互成就的。2003年以后,中欧关系就进入了调整期。这段时间,双方接触更多了,摩擦和矛盾也变多了,互相的认知发生了变化,分歧也逐渐显现。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,双方的沟通渠道中断,再加上俄乌冲突对中欧关系的冲击,中欧之间的距离被拉大,相互疏离,甚至有时候龃龉不断,导致双方利益受损。
实际上,中方一直坚持维护中欧关系的大局,一直坚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欧洲方面则因为民意基础比较复杂,一些政客随选票“起舞”,给中欧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同时,一些媒体散布的不实之词和谣言也对中欧关系起到了“促退”的作用。我觉得,在这种情况下,要改善中欧关系,破局还是要从民间开始。只有人民之间的交往扩大和加深,才有可能改变现在中欧关系的整体氛围。
澎湃新闻:在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,您曾提到中欧关系“进入了需要慎重调整的复杂阶段”。就您的观察和研究来说,中欧关系的“复杂”具体指哪些方面?
周弘:我讲的复杂性,首先是结构上的复杂性。中欧在制度上存在非对称性或不对称性,比如制度上的差异,比如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,这些就是不对称性。欧洲人把这种不对称性简单化了,就是所谓的“因为制度不同,所以你是我的对手”。这种所谓的“制度性对手”是一个错误的认识——制度不同为什么一定是对手?
中国承认和欧洲在制度上是不同的,但我们对民主、人权、繁荣这些目标的追求是共同的,只是我们的路径和模式不一样。这种不同来自历史和文化的不同积淀,不能强求一致,也不可能一致。这个非对称性是中欧关系的现实,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。所以在整个过程中,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某种合理的、共处的局面。
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,就是尽可能多地恢复过去的交流渠道,把所有不同的意见拿到桌面上,然后去谋求解决方案。其实,欧洲人也意识到交流渠道被隔断对中欧关系造成了危害,认识到他们有一些错误的理念和说法。这都是要通过交流解决的,恶语相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“‘去风险’是一个没有内涵的政治话术”
澎湃新闻:近年来,欧盟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影响中欧贸易的措施,特别是去年针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措施,更是引发全球关注。这些摩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?中欧又如何避免所谓的“去风险”滑向“脱钩断链”?
周弘:汽车行业是欧洲的支柱行业,特别是德国。在过去很多年里,欧洲汽车行业享受了技术优势并从中大量地获益。中国电动车这样节能环保、便宜实惠的产品,肯定会引起市场竞争,会损害到有些人的利益,中欧出现摩擦、矛盾是很自然的现象。
问题是怎么样管控分歧和摩擦。比如说根据世贸组织(WTO)的规则,根据中欧间的贸易协定的规定,我们可以在现有的框架里去讨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。我相信中国和欧洲专业的谈判人员能够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。
中国和欧洲不可能、也不想“脱钩断链”,因为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伤筋动骨的损伤。至于“去风险”,我觉得就是一个没有内涵的政治话术。什么叫风险?你有可能把所有的风险都去掉吗?这种话术本身没有意义。有意义的是在规则的基础上,通过谈判得出一个理性的、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,这是可能的。如果说现有的规则还不够,我们可以创造新的规则,我相信双方的专业人士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。
澎湃新闻:近期,中欧在经贸和政治领域出现了关系缓和的迹象,有观点认为,欧盟试图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“特朗普2.0时代”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,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?
周弘:“特朗普2.0”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,一些欧洲朋友就跟我说,他们预期到“特朗普2.0”会是个麻烦,但没想到它是这么大的麻烦。特朗普不仅发起了对欧盟的关税战,在他对未来世界的设计里,盟友是没有地位的。这些都警醒了欧洲,让欧洲必须要调整它的政策。
应对“特朗普2.0”,欧洲首先是要自强,这意味着从紧靠着美国变为向中间地带移动。具体到中欧关系,这就给双方合作打开了一些窗口,比如在经济上重新恢复与中国的一些合作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不会跟中国发生摩擦,因为欧洲最终的目的是要强化自己,因此合作的领域是有选择的,比如人工智能、绿色经济、高科技领域等,这些领域是欧洲现在比较薄弱的领域,它需要和中国合作,并制定共同的规则来做强自己。
我觉得这个窗口期还是需要紧紧抓住。欧盟调整政策是费时耗力的,它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,我们要解剖这些不同的声音,抓住那些积极的东西,然后扩大合作,因为合作加强了欧盟,也加强了我们自己。
中欧要用理性解决对立和分歧
澎湃新闻: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,欧盟与中国在安全议题上的对立日益凸显。中欧都强调维护主权国家的权利,但为何会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?这种分歧又对中欧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周弘:在中欧之间,乌克兰问题是一个解不开、理不顺的死结。
我认为,这里面情绪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。我有一个德国朋友,他就讲他的家里头住了几个乌克兰的难民,每天告诉他的就是“家国破碎”这种悲惨故事。而中国跟乌克兰隔得很远,我们感受的跟他们作为近邻的感受不一样。这种情绪被媒体放大渲染,再加上一些媒体制造谣言,导致很多欧洲人觉得“俄罗斯就是在中国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”。
在这种情况下,理性的声音听不到了。乌克兰问题很复杂,它既牵涉了国际准则,也涉及历史根源,破解是需要智慧的,但现在没有理性哪儿来的智慧?要想有政治智慧,首先需要理性,要把情绪化的烟雾驱散了以后,真正地用脑子来想问题,而不是用嗓子来喊问题。
澎湃新闻:面对美国单边主义,中欧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。但双方在俄乌冲突、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差异,是否削弱了合作基础?
周弘:我觉得没有。在全球治理这个议题上,中国和欧洲是有很多一致性的,例如中欧都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制,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等。
在很多低政治领域,比如应对气候变化、打击有组织犯罪、减贫、发展绿色经济、食品安全等等,中国和欧洲的合作是很密切的。欧洲人自己也说,在全球治理的问题上必须跟中国合作。
同时,中国和欧洲还在探讨更多、更新的全球层面合作的领域和可能性,比如在SDG(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)的最后阶段的工作,比如对“未来契约”的设计,这都是一些前沿的问题,还需要中国和欧洲更紧密的合作。
“我对中欧关系是抱有信心的”
澎湃新闻:在您从事研究工作和与欧洲国家的专家学者交流的过程中,您觉得中欧之间政策理念、文化价值观、话语体系等存在的差异,是否影响了中欧双边互动?
周弘:我个人觉得,中国和欧洲在政策理念、文化价值观这些方面的不同,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与合作。因为我们在交流和合作的时候,往往讨论的是非常具体的专业问题,比如为什么在解决类似的问题时欧洲的政策是这样的,而中国政策是那样的?哪种政策更好一些?有无相互借鉴的可能,等等。
中国和欧洲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,方法不一样,做法不一样,但我们不会像有些个别的欧洲人那样,去指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有的时候,看问题的方法、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,正好可以弥补相互之间的一些不足。我觉得对于交流来说,政治理念、文化价值观不是障碍,无知是障碍。
澎湃新闻:今年年初以来,中外网民通过社交平台,比如小红书、抖音等,开启了一轮所谓的“社交平台对账”热潮。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,您如何看待Z时代通过互联网打破“信息茧房”、重新认识对方的行为?
周弘:我觉得从总体来说,在任何一个时代,只要技术进步,它都会带来一些改变,对社会带来一些改变。
如果我们有意识、有目的、有方向地去引导这些技术的使用,那就会给人类造福。沟通领域的技术发展非常快,它应该导向更便利的沟通;更便利的沟通应该导向更好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。但是,技术也有可能便利于人为的造势,也有可能便利于情绪的宣泄,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东西。
澎湃新闻:从个人角度看,您对中欧下一个50年又有怎样的期待?
周弘:中欧关系有今天的成就,是中国人和欧洲人坚持不懈、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数千年来,不管是山川大漠的阻隔,还是战争和政治的破坏,中欧都有人要不遗余力地去接触对方,所以才有了马可·波罗在欧洲的风靡,才有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去欧洲勤工俭学,才有了这样一些交往。不管出现了什么困难,总有那么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去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。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,我对中欧关系向前向好发展是没有异议的。
我们所能做的事情,就是致力于中欧关系向好发展,尽可能地排除干扰,因为中欧关系好,对双方都好,对中欧人民也好。要搞好中欧关系,需要增加相互了解、理解、尊重,乃至欣赏,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有很多这样的先例,所以中欧关系才有今天这样密切的程度。目前,西方一些文人、政客搞一些事情试图干扰中欧关系发展,都是很短视的行为,不可能阻挡历史车轮向前转的。即使出了一些问题,走了弯路,人民会把中欧关系拉回到正轨上来的。我对中欧关系是抱有信心的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再遇见|社科院荣休学部委员周弘:中欧要紧紧抓住“窗口期”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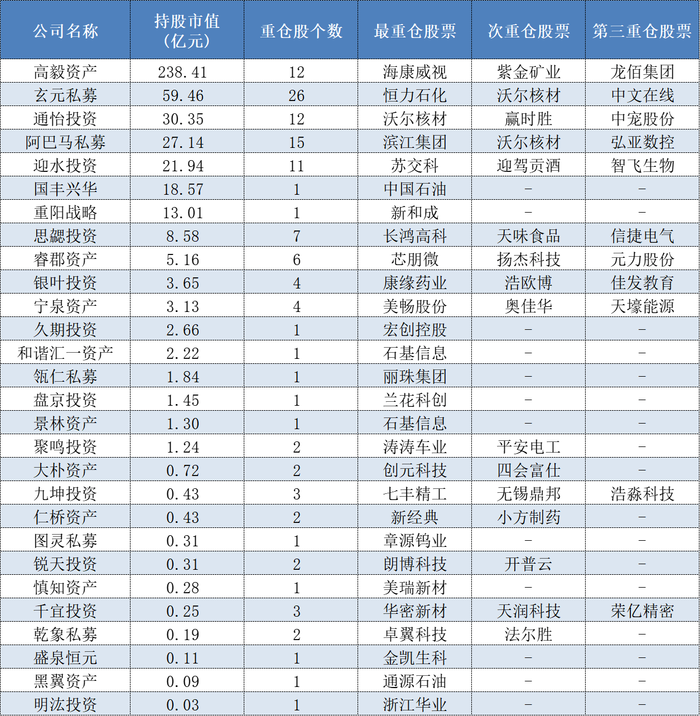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京ICP备2025104030号-15
京ICP备2025104030号-15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